
2022年3月16日晚上七点,哈佛大学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终身教授、四川大学高端外籍教授范德康先生以“天文历法(སྐར་རྩིས་རིག་པ)与汉地五行占算(ནག་རྩིས)在藏地”为题进行了线上讲座,讲座由石硕教授主持,玉珠措姆教授翻译。本场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藏学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五讲,来自四川大学、哈佛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师生和公众700余人聆听了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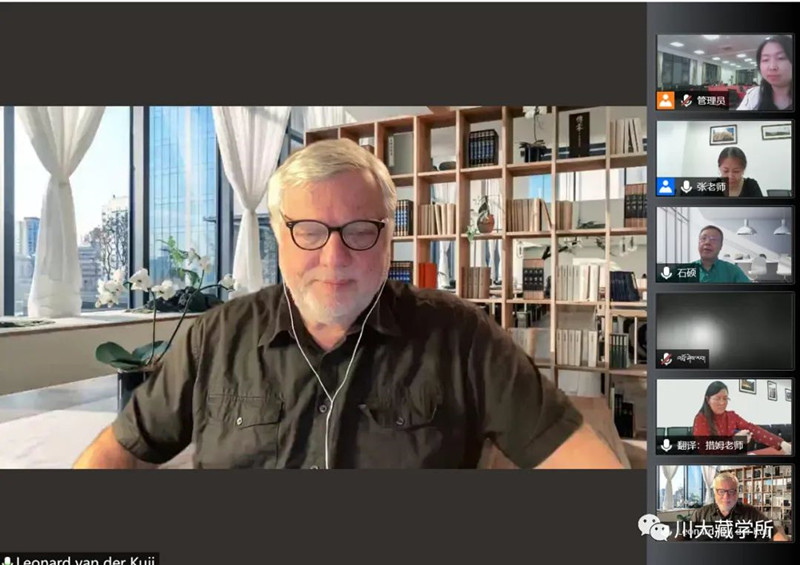
(线上讲座截图)
一、天文历法(སྐར་རྩིས་རིག་པ)
范教授开门见山地提出,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1182-1251年)可能是第一个将算学(རྩིས་རིག)或天文历法(སྐར་རྩིས་རིག་པ)纳入五明之工巧明(བཟོའི་རིག་གནས或བཟོ་རིག)的藏族学者。在无著(Asaṅga,4-5世纪)编纂的《菩萨地》(Bodhisattvabūmi)中,工巧明也被称为世间工业明处(laukikāniśilpakarmasthānavidyā,འཇིག་རྟེན་པའི་བཟོ་དང་ལས་ཀྱི་གནས་ཤེས་པ)或世工业明处(laukikaśilpakarmasthānavidyā,འཟིག་རྟེན་པའི་བཟོ་དང་ལས་ཀྱི་གནས་ཀྱི་རིག་པ),两者在藏文中的简称即为工巧明。无著将世间知识归纳为五明(pañcavidyāsthāna,རིག་པའི་གནས་ལྔ),并认为精通五明才可成为遍知一切的大乘佛教大师。萨班在《智者入门》(མཁས་པ་རྣམས་ལ་འཇུག་པའི་སྒོ,1220年)中重申了五明的重要性,他引用了《大乘庄严经论》(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的一部经文,将其中的十八个知识领域归为五明,但这一经文在现存有关《智者入门》的四本书中都未被识别出。《甘珠尔》中有两部经文提到了“十八种知识领域”,即《比丘尼律分别》(Bhikṣunīvinayavibhaṅga)和《大方等大集经·日密分》(Sūryagarbhasūtra),其中前者有“星象学”(སྐར་མའི་རིག་པ)的表述,且成书时间可能为11世纪早期。《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utpatti)里虽列举了不同的十八个知识领域,但也将“天文历算”(jyotiṣa,སྐར་མའི་དཔྱད)包含在其中。第司·桑杰嘉措(སྡེ་སྲིད་སངས་རྒྱལ་རྒྱ་མཚ,1653-1705年)等人错误地将十八种知识领域的划分归为世亲(Vasubandhu)的《阿毗达摩俱舍论》(Abhidharmakośa),但《俱舍论》中并无这一划分。第司还引用了《普曜经》(Lalitavistara),其中提到有“占星术”(jyotiṣa,སྐར་མའི་ལུགས)。他还参考了《阿含杂事解脱》(Āgamakṣudrakavyākhyāna),但实际上他引用的是调伏天(Vinītadeva,7世纪)的《<律分别>析义》(Vinayavibhaṅgapadavyākhāna)。
J. Kotyk在最近的相关研究中指出,虽然僧众有时不赞同天文历算的实践,但总体上来看,佛教对历算的逐渐接受反映出第一个千年纪里天文学在印度文明中影响力的扩大。早期的律学经典显示,人们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些天文学知识以决定长净仪式(poṣadha, གསོ་སྦྱོང)的日期。玄奘(602-664年)也观察到在天竺,孩童从七岁起就要学习五明,其中第二项工巧明包括“技艺、阴阳与算术”。显宗和密宗经典里历时地记录了天文学知识,11世纪早期翻译《时轮续》(Kālacakratantra)就是这一现象的高潮。萨迦班智达认为,工巧明中星象学占有重要位置,在他之后,天文历算作为工巧明的分支,获得了小五明(རིག་གནས་ཆུང་བ)之一的地位。这说明,天文知识的流行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现象,且在之后的佛教话语里取得了相对优势。
“རྩིས”一词含义较广,有“算术、计算、思考、考虑”等意涵,在不同的用法中有不同的翻译方式。“རྩིས་པ”的意思是“会计、会算术的人、数学家、天文学家”等,延伸开来就是“制作命宫图、历书、星历表、天文表的人”。因此历算学(རྩིས་རིག)意味着“计算的知识、天文科学的知识”。“སྐར་རྩིས”这一术语仅出现在雄顿译师多吉坚赞(ཤོང་སྟོན་ལོ་ཙཱ་བ་རྡོ་རྗེ་རྒྱལ་མཚན,1225-1280年)翻译的吉祥称(Yaśas)的《时轮略续》(Laghukālacakratantra)中,华莱士(V. Wallace)明确指出这一翻译是错误的,在文本语境中不应是“天文学家”,而是指“天体”。此外还有“དཀར་རྩིས”的表述,但与天文科学没有丝毫关系,“དཀར་རྩི”是指“石灰或白色颜料”,因此“དཀར་རྩིས”是指“用石灰或用白色颜料”。正确的写法应该是“སྐར་རྩིས”,“དཀར་རྩིས”则是误写。之所以容易产生这样的误写,一方面是因为谐音,另一方面是因为容易与“ནག་རྩིས”(汉地五行占算)对立起来,因为དཀར是白色,ནག是黑色。在很多文化中都有黑白的二元对立且暗含有道德伦理上的高低意味。因此,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年)1652年从清廷回来后,在1656年写作历算书籍时,尽力消除“ནག”的负面含义,指出“ནག་རྩིས”与颜色无关,仅指从汉地传来的天文科学。
萨迦班智达有关天文历算的评价在达仓译师(སྟག་ཚང་ལོ་ཙཱ་བ་ཤེས་རབ་རིན་ཆེན,1405-1477年)处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令人惊讶的是,达仓译师坚定地认为工巧明应该位于五明之首,原因在于只有拥有有关建筑的知识,才可修建装藏佛陀舍利的佛塔,才可实现全部所求,更重要的是,它是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这一观点与佛教“身语意”的观念相连,佛像、佛经、佛塔代表佛的身、语、意,其中意工巧最为基础和重要,它要求学习、反思和冥想,如此方有可能解脱。在达仓译师有关“意”工巧的描述中,他写道意工巧包括天文历算,需观察和学习日历五要素(pañcāṅga,ལྔ་བསྡུས)、升交点(rāhu,སྒྲ་ཅན)、降交点(ketu,གདོང་མཇུག)、日食或月食(ཉི་ཟླ་གཟའ་འཛིན)、合时(lagna,དུས་སྦྱོར)等。达仓译师将工巧明在人类知识领域中的地位总结为,没有一项人类知识不被包含在工巧明当中,因此不可以将其贬低为谋生的知识领域。这可能是对《大方便佛报恩经》(དྲིན་ལན་བསད་པའི་མདོ)等经文将世方术作为获利手段的观点的回应。
萨迦班智达没有明确地划分小五明,色多班钦(གསེར་མདོག་པན་ཆེན)谈论到小五明的分类,但似乎分出了六明,即语法学(śabda,སྒྲ)、辞藻学(ཚིག་རྒྱན)、韵律学(chandas,སྡེབ་སྦྱོར)、戏剧学 (nāṭaka,ཟློས་གར)、诗学(kāvya,སྙན་དངགས)和星象学。关于星象学色多班钦写道,有人宣称了解星象学后,就不会对世间的福祉感到困惑,萨迦班智达及其后继者都在天文历算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
这样看来,早期的梵文和藏文文献中,天文历算并不属于“内明”,即佛教知识的范畴。但达仓译师主张包括内明在内的知识都属于工巧明,这就使宣称工巧明具有某种救赎性地位成为可能。
二、汉地五行占算(ནག་རྩིས)
如果工巧明包含了包括内明在内的所有知识领域,那么天文历算可能有救赎性的一面。如果汉地五行占算和天文历算同等出现的话,那五行占算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写道:文殊菩萨将计算年、月、日、时、生命力(སྲོག)、身体(ལུས)、命运(དབང་ཐང)、气数(རླུང་རྟ)和八卦(སྤར་ཁ)等的方式授予孔子……汉地的计算方式也可以被包含在工巧明中。第司·桑杰嘉措也附和道,虽然汉地五行占算这一知识领域在天竺不为人所知,但就其主旨意义而言,与天文历算是相似的。
正如迪特·舒(Schuh)指出的那样,第司将佛语(བཀའ)分为三部分,将汉地五行占算放在“加持语”(བྱིན་གྱིས་རླབས་པའི་བཀའ)中,声称是由佛的一位声闻弟子或菩萨传播。接着主张汉地五行占算由文殊师利菩萨弘传,由此将其纳入了真正的佛教教学之中。第司于1683年开始写作《白琉璃》(Vaiḍūrya dkar po),1685年完成,其同时代人将这部同时包含了印藏天文知识和汉地五行占算的作品称为“前所未有的著述”(སྔོན་ན་མེད་ཀྱི་བསྟནབཅོས)。像达仓译师一样,第司·桑杰嘉措也重新将古印度或印藏天文知识以及汉地或汉藏天文知识确认为工巧明的一部分。
邬金林巴(ཨོ་རྒྱན་གླིང་པ,1323-?年)《五部遗教》(བཀའ་ཐང་སྡེ་ལྔ)中的《大臣遗教》(བློན་པོ་བཀའ་ཐང་ཡིག)也有很多关于汉地五行占算的内容,但多具有误导性。这部经书的相关章节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最长的一部分,从梵文宗教典籍中提到的天文学类型开始写作,这一部分只有印度天文历算的出现。邬金林巴接着提及一些阿阇黎(སློབ་དཔོན)的著作,写道文殊菩萨曾在五台山上宣讲五龟(five turtles)、四根本续(རྩ་བཞི)和集合七续(འདུས་པའི་རྒྱུད་བདུན),后两者并不像迪特·舒推测的那样与《时轮》有任何关联,且虽然《时轮略续》的作者吉祥称被视为文殊的化身,文殊菩萨在《时轮》的传播过程中并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第三部分讲述“世间占星术”(སྲིད་ཀྱི་གཙུག་ལག)中的“རྩིས”,第四部分对“རྩིས”进行了整体概括,第五部分谈到历算并非完全可靠。范教授认为虽然通篇没有出现“ནག་རྩིས”一词,但经书中有些泛指“རྩིས”的段落实际上是指汉地五行占算。
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得力助手第司对汉地五行占算产生了深厚而又前所未有的兴趣,二人在保存可能是汉地占星术著作的早期藏文译本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们提供资金,用上乘纸张将旧译本重印,用藏文楷书(དབུ་ཅན)替换草书(དབུ་མེད)使其更易阅读。格鲁派的领导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与汉地五行占算相关的主张、实践以及在俗人团体里大受欢迎的占卜算命融入到佛教的框架中,并相信其起源于文殊师利菩萨。这些重印的译本现存于世,其中提到译者有文成公主,范教授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第司在提到汉地公主时,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指早期对汉地五行占算的翻译,而不是指文成公主翻译了相关著述。此外,第司也将金城公主的名字误写为文成公主。
但并非所有的格鲁派精英成员都支持五行占算起源于汉地的说法。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བློ་བཟང་ཆོས་ཀྱི་ཉི་མ,1737-1802年)和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བློ་བཟང་ཚུལ་ཁྲིམས,1740-1810年)就对汉地五行占算的起源和内容存疑,认为可能是早期藏族人的匿名伪造。如察哈尔格西提出有关五行占算起源的多种叙述并不可靠,并进一步指出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司宣称《四部医典》(རྒྱུད་བཞི)含有佛陀教导的主张同样不可靠。三世土观活佛认为在五行占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乌龟”(གསེར་གྱི་རུས་སྦལ)是藏人的虚构,但van Schaik指出在敦煌文献Or. 8210/ S.6878中就有对金乌龟的描述,也就是说早在三世土观活佛之前八百年就已经有了此概念。
其他一些文章也对五行占算的起源提出了质疑,但有意思的是,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司等熟知藏族宗教和政治历史的学者却对此充耳不闻。五世达赖喇嘛曾两次在自传中提到他研究过汉地五行占算,第一次是在1637年,他可能和赤列嘉措(འཕྲིན་ལས་རྒྱ་མཚ,五世达赖喇嘛的侍从及第司)一起在素·却英让卓(ཟུར་ཆོས་དབྱིངས་རང་གྲོལ,1604-1669年)的指导下学习了相关天文知识。1657年,在一篇有关天文学的文章中,五世达赖喇嘛直接表明,五行占算确实起源于汉地。
毫无疑问,汉地五行占算在数世纪的发展中是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15世纪以前,藏文经典中鲜有提及汉地五行占算及其衍生物,如禳灾仪轨(གཏོ)和风水(ས་དཔྱད)等。此外,精通天文历算者如布顿大师(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1290-1364年)、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རང་བྱུང་རྡོ་རྗེ,1284-1339年)等人都全然不提汉地五行占算。这一缄默是有意义的,因为并非所有人都不赞同印度的命理学、预兆学(Svarodayatantra)和天文学等知识。它表明当时一部分卫藏人在文化上倾向于亲近包括尼泊尔在内的次大陆。与此同时,卡垫上的众多图案与寺庙和家庭内的装饰都起源于内地。迪特·舒写道,从吐蕃衰落到佛教的后弘期之间,诸如汉地五行占算、风水和地祇(ས་བདག)一类的文化因素已经悄然渗入藏文化的图景中,这是佛教以外的一种非主流文化,但其对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即使17世纪新教派将其融入进藏传佛教里,也未能改变这一亚文化的重要意义。范教授有关藏文化天文历算学发展过程的梳理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迪特·舒的结论。
讲座问答环节,校内外师生在线上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范教授详细解答了就讲座相关内容所提出的问题,石硕教授对讲座主题的重要性及讲座内容的专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玉珠措姆教授精准专业的翻译表达了诚挚感谢,本场精彩的讲座圆满结束。
温馨提示:讲座全文将刊发于纪念迪特·舒教授(Dieter Schuh)文集,如需引用请关注原文,务必注明出处。
(感谢玉珠措姆教授对本文的校正,感谢罗鸿教授对其中梵文词汇的修订,感谢银巴教授对专业术语翻译的建议。)
翻译整理:杨瑜玥
审稿:玉珠措姆、张长虹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