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9日晚,来自牛津大学的乌瑞克·罗斯勒教授(Prof. Ulrike Roesler)应邀进行了一场题为“噶当派在卫藏地区的兴起”的线上讲座。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藏学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七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研究员主持,特邀哈佛大学内亚系博士候选人尹筱天翻译。
公元11到13世纪的藏传佛教后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各个佛教团体的迅速发展给西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新的寺院的建立,导致了新的社会和经济网络的出现。其时,佛教在西藏尚没有界限分明的教派之别,而是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多极互动的动态宗教景观。
噶当派是该时期出现的众多的佛教传统之一,他们将自己的传承追溯到印度学者阿底峡(Atiśa Dīpaṃkaraśrījñāna,982-1054)及其藏族弟子仲敦巴(’Brom ston Rgyal ba’i ’byung gnas, 1004-1064)。噶当派常被描述为提倡僧侣式的生活方式,不鼓励密宗修持,因此看起来似乎没有其他教派那么多姿多彩,受到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实际上,噶当派的活动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噶当派出现了一些极有原创性的上师,在卫藏地区佛教教派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噶当派的影响深远,除了其继承者格鲁派,还包括其他的教派。噶当派的一些上师是藏传佛教和藏文文献的创新者,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芒域贡塘木刻本收录了早期上师们的作品,包括经典的米拉日巴传记和道歌。最后,正如范德康教授(Prof. Leonard van der Kuijp)曾经指出的那样,噶当派甚至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转世观念的教派,比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1206-1283)被认定为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1110-1193)的转世早了大约100年。
本讲座从四个方面对噶当派进行了讲解。
一、噶当派的起源
噶(bka’),意为“佛语”;当(gdams),意为“教诫、教授”;噶当意即以佛语为修行要诀之教授。噶当派以阿底峡为其发宗绪者,阿底峡的弟子仲敦·杰瓦迥乃为开其派规者。
“阿底峡”是一个印度的荣誉头衔,意为“尊贵之人”或“卓越之人”,对应于藏文的称号觉沃(Jo bo)或觉沃杰(Jo bo rje),被授予印度学者Dīpaṃkaraśrījñāna,后来这一荣誉称号比他的本名更广为人知。1042年,他年届60岁时,从印度的超戒寺来到西藏,在西藏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2年。在这期间,他从事教学、合作翻译、举办佛教仪轨活动等,直至1054年在拉萨附近的聂唐寺圆寂。
噶当派初创的11世纪,阿底峡在西藏拥有众多追随者,他们背景各异,有僧人、瑜伽士、在家居士和施主等。其中,牧民之子、在家居士仲敦巴被认为是他的主要继承人。仲敦巴在阿底峡圆寂之后,于1056/1057年在拉萨北部建立了热振寺。西藏佛教史将热振寺的建立视为噶当派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仲敦巴也被视为噶当派的祖师。
噶当派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1到12世纪的创建时期,以卫藏腹地热振寺及其周边为基地;第二个阶段是13到14世纪的跨区域发展时期,以后藏的纳塘寺及其辐射地为基础。
二、热振寺的创建
热振寺的建立是噶当派成立的标志性事件,热振寺也被视为噶当派的主寺。详细记载热振寺建立的文献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三部写于12到13世纪的早期记述:一是《阿底峡广传》(Rnam thar rgyas pa);二是《阿底峡和仲敦巴传》,由纳塘寺第七任座主钦·南喀扎(Mchims Nam mkha’ grags, 1210-1285)所作。三是卓·协饶迈杰(’Brom Shes rab me lce)所作的《热振寺解说》(Rwa sgreng gnas bshad),可能是他于1299年在纳塘寺所写。
《阿底峡广传》中记载,当阿底峡要求仲敦建立一座寺院时,仲敦回答道,“一,我对世事了解很少;二,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三,我寻求布施的力量微弱。”这些不仅仅是仲敦的谦虚之辞,而是反映了他的社会和宗教地位。在社会层面,仲敦出身牧民家庭,而阿底峡的其他弟子出身贵族;宗教层面,仲敦终生都是一个居士,地位低于僧人,这两方面都使仲敦很难成为领导僧众的候选人。不过,仲敦还是遵从老师的指示,在阿底峡圆寂之后,想在聂唐为阿底峡的遗骨建造一个佛殿(拉康),但是遭到了当地僧团的驱逐。仲敦带着阿底峡的灵骨去向了他老家乌如羌(Dbu ru Byang)的方向,又经过两次失败之后,终于得到了他的旧识仓喀贝穷(’Phrang kha Ber chung)的邀请,愿意资助他在热振河谷建寺。贝家几代人都是热振寺的赞助人,这表明仲敦和仓喀贝穷之间的关系是热振寺成功兴建的必要备件。仲敦的传记中记载了他建立寺院选址的现实考量,选择热振河谷,一是因为有粮食供应,二是政治稳定,这对于建立寺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反映出11世纪卫藏地区的政治变化,当时没有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势力,相邻地区和部族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仲敦和他的同伴于1056年(火猴年)抵达了热振,这一行人由仲敦这个居士和至少四名瑜伽士组成。他们想要建造一座寺院,但却没有持律之人!热振寺最初的建筑,除了安供阿底峡遗骨的佛殿以外都是居所,供仲敦和瑜珈士们居住。这表明热振寺最初只是一个修行场所,而非教授和传播寺院规则的机构。热振寺的创建故事非常有意思,13世纪钦·南喀扎撰写的仲敦巴传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仲敦巴传》以对“热振”(rwa sgreng; ms: ra sgyeng)这一词的解释开始:“དེ་ཡང་དང་པོ་ལྡན་མའི་ཡུལ་ཡིན་པས་ལྡན་སྐད་དུ་ར་སྒྱེང་། བོད་སྐད་དུ་ཆུ་མིག་རིང་མོ་ཞེས་བྱ་བ་ཡིན་སྐད།”,认为“因为它原本处于丹玛(ldan ma)地区,所以在丹玛语中被称为热振,在藏语中叫chu mig ring mo”,南喀扎并未将丹玛与康区的“丹玛”联系起来,而应是当地的一个名字,目前关于该词的词源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
在热振寺的奠基故事中对热振河谷的吉祥景观进行了详细描述,从宇宙之主转轮王的观念讲起,然后按西藏方式从上到下分层描述,接着又按汉地四神的观念进行介绍。此外,传记还提到了这个地方曾经是吐蕃时期的重要贵族觉若(Cog ro)家族的墓地所在;热振河谷地理位置优越,东西南北都有通向其他地区的通道,因而物产交流十分丰富,能够满足维持寺院所必需的物资供应等非常重要的信息。
由于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噶当派上师曾经在热振寺受过训练,该寺也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寺院。仲敦的徒子徒孙在热振的邻近地区也建立了不少寺院和修行地,于是,11世纪末12世纪初,噶当派在当地得以迅速扩张。
三、噶当派的身份建构
仲敦之后,噶当派的三个主要传承源自他的三名弟子,被称为“噶当三昆仲”。一是普多瓦的传承(Po to ba Rin chen gsal, 1027-1105),以教典(gzhung pa)而著称;二是坚阿瓦的传承(Spyan snga ba Tshul khrims ’bar, 1038-1103),被称为“教授传承”(man ngag pa or gdams ngag pa);第三是普琼瓦的传承(Phu chung ba Gzhon nu rgyal mtshan, 1031-1106),被称为传记传统或者密教传统。
但在11世纪噶当派刚出现的时候,情况没有这么清晰。我们通常会认为阿底峡或者仲敦是这个新教派的创始人,但“创始人”这个提法值得探讨。正如丹·马丁(Dan Martin)所说,相比于教派被谁、什么时候创立,更重要的问题是广大社会环境中的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意识到噶当派这个教派的存在。
11世纪的少数资料中似乎没有任何特定的术语来将阿底峡的追随者们称为一个教派或者一个传承。12世纪初的文本中出现了“Jo bo的传承”,即“阿底峡的传承”;普多瓦时代有人偶而开始自称噶当派了,但形容噶当派团体的术语仍然不固定。13世纪钦·南喀扎的《纳塘金鬘》中则更强调“热振的佛教传承”及仲敦巴。纳塘传统对于提升热振寺在噶当派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推动了噶当派的跨区域传播。1153年建立的纳塘寺成为噶当派向西传播的新据点。
噶当派的身份建构过程在15世纪晚期进入最终阶段,这个阶段也正是格鲁派崛起的时间。格鲁派最终吸收了噶当派,这个过程被如实反映在这段时间创作的三部噶当派的历史著作中,分别是1484年益西孜摩(Ye shes rtse mo)和索南拉益旺波(Bsod nams lha’i dbang po)所作,和十年后列钦·贡嘎坚赞(Las chen Kun dga’ rgyal mtshan)所写的噶当派历史,将当时宗喀巴的传统称为所谓的“新噶当派”,创造出了宗喀巴是噶当派的真正继承者的画面,也意味着噶当派作为一个独特教派的终结。这一时期,随着统治者家族及其势力介入佛教传承的政治活动,各传承宗教政治地位的竞争使得对于宗教派别身份的建构和突出各自的成就变得更为迫切,促进了宗教身份认同的建构。
四、噶当派与卫藏地区的律宗
噶当派和卫藏地区律宗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西藏的《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承就中断了。后有“卫藏十人”去往藏东的安多地区,在青海丹底寺受戒,并于公元978年将寺院戒律带回了卫藏,史称“东律”(smad ’dul)(详见Heather Stoddard 2004)。
新受戒的僧人在拉萨及周边的地区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戒律团体,占据了卫藏地区原有的一些寺院,并新建了一些寺院,与当地的世俗赞助人建立了联系。为了争夺一些重要寺院的控制权,这些团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彼此敌对的行动一直持续到了13世纪(详见Per Sorensen and Guntram Hazod 2007)。
从11世纪中叶开始,也就是热振寺创建前后,这些律宗僧人就已经建立了一些讲经院(bshad grwa)来研究戒律。后来当寺院机构变得庞大,律宗讲经院就成为这些大型寺院的一部分,于是有很多当地的早期律宗寺院就被废弃了。考虑到噶当派也于这一时期开始发展,他和上述的某个律宗团体之间应该有联系,但仔细阅读藏文史料后发现,这两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
首先,阿底峡的追随者们和任何特定的律宗团体没有关系;其次,阿底峡本人是没有办法在西藏传授戒律的,因为他来自一个不同的印度戒律传承,也就是西藏从未使用过的大众部戒律,所以他本人并没有在高原僧院体系的建立当中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再者,在阿底峡圆寂之后,他的弟子们和卫藏律宗团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所以阿底峡的弟子才会离开聂唐,去建立自己的寺院和修行地。最后,阿底峡的大多数亲传弟子和戒律没有什么关系,仲敦巴终生都是居士,热振寺建立后,戒律也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部分。《青史》中就指出,热振寺有60名修行者(sgom chen pa),而不是僧人(dge slong)。
尽管一般来说,僧人比居士享有更高的宗教地位,但早期噶当派的宗教活动是由瑜珈士和在家居士推动的,僧人受戒出现得稍晚,并且对热振寺的噶当派上师来说,他们的律宗归属和他们所传承的教义、修持之间似乎没有很深的联系。
讲座最后,张长虹研究员指出,罗斯勒教授从早期的藏文史料出发,对西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噶当派的早期活动进行条分缕析,对一些看起来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重新审视,所做的研究严谨细致,加之尹筱天博士专业的、精准的翻译,共同为师生奉上了一场精彩无比的学术讲座。罗斯勒教授还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晚9时许,讲座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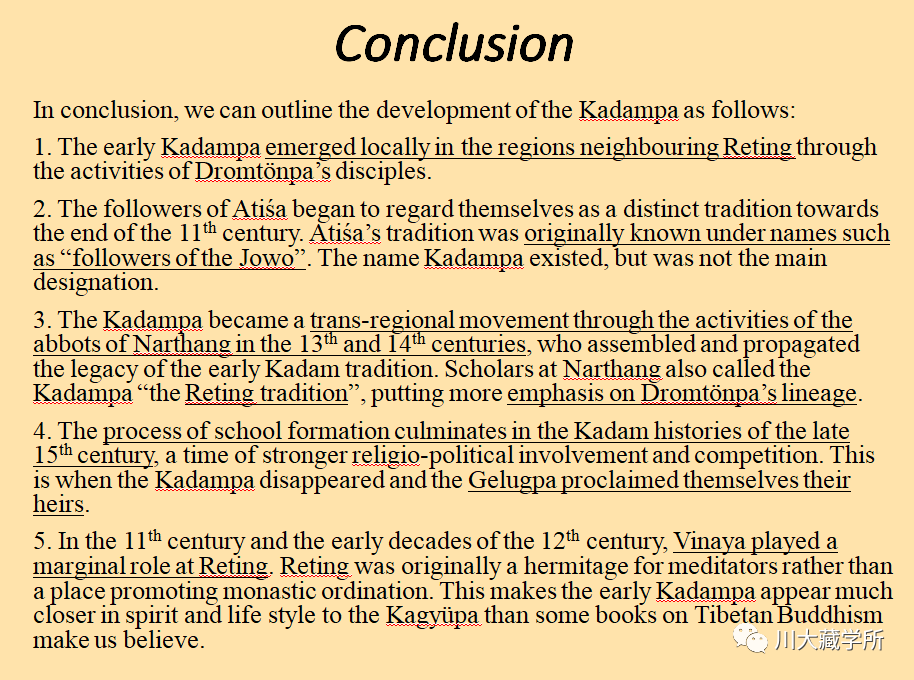
尊重原创,遵守学术规范,若需引用,请注明出处。
整理:王俪达
审稿:张长虹
编辑:孙昭亮